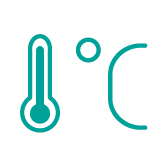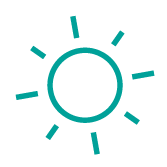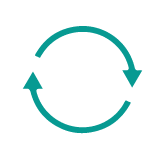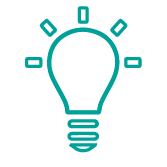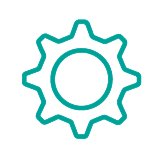彼得·圣吉&奥托·夏默尔:当我们对现实感到绝望时,如何表达对未来的希望?
文/孙海燕
在这个夏天,U型理论创始人奥托·夏默尔博士和“学习型组织”之父彼得·圣吉博士在上海外滩三号“三言舍 Three Talk”的活动上,对目前全球所面临的三大鸿沟——无论是生态、社会,还是精神鸿沟,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提出了面向未来的可能的变革之路。《商业生态》记者对两人的演讲以及现场对话进行了整理。
从自我到生态的转变,将是一种旅程

奥托·夏默尔博士 U型理论创始人
我是在德国成长、长大的,20多年前,我做了一个决定,希望可以搬到麻省理工学院加入彼得·圣吉的学习中心这样一个平台。彼得当时出版了《第五项修炼》这本书,以此为基础打造了那个平台。日后,这本书也被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管理学的书籍之一,那时候我对他的一些理论非常感兴趣,所以我被吸引到麻省理工学院(MIT),从此开始了我们俩的合作。
到底是什么吸引我到MIT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方(冰山的图),这是冰山一角,也就是说10%在上面,但是底下的90%也很重要。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是底下的这部分却决定了整个系统的一个运作。大家如果看10%的这个部分,这是一种症状的表现。如今,当我拜访不同的国家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大家所面临基本的挑战是如此相似。无论是社会,亦或经济层面,每个国家面临着相似的挑战。我把这些挑战总结为不同的鸿沟,包括社会的、生态的、以及精神的鸿沟。
生态鸿沟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是指我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而这些问题可以以1.5这个数字来总结。如今,在全球经济中我们使用了1.5个地球的资源。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比如说,经过上一代的发展我们失去了许多的石油,在上海,从上世纪末的二十年来,上海已经下沉了2.5厘米,上海一直在下沉。我们都看得到这些问题,但是应对这些问题却非常困难。
第二是社会鸿沟,也就是那些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之间的鸿沟。这些鸿沟产生了一些多极化、以及极端的现象,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都能够观察到这样的现象。
生态鸿沟,主要是关于自我和自然之间的脱轨和脱节,社会鸿沟可以说是自我和他人之间的脱节,而精神鸿沟则是自我和自我之间的脱轨。自我和自我之间的脱节是指什么呢?也就是指由过去一系列事件和经验导致的“今天的自我”和能够达到的最大潜力的“明天的自我”之间的脱轨。如果这两种自我——“今天的自我”和“明天的自我”——之间没有交流,没有再连接的话,现实就会显得异常疲惫、抑郁,甚至面临自杀的风险。2010年,世界上自杀的人数比那些由于战争和自然灾难而引发的死亡人数加起来还要多。
因此,当我们退一步来想想,从系统思考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什么?今天大部分的系统都可以由这句话来描述——我们集体创造了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比如说这种1.5倍的资源,我们的社区中不断增多的冲突。没有一个人早上起来照着镜子对自己说——“好吧,今天我要继续破坏自然,我要对别人行使暴力,并且,我要努力变得更加不快乐。”并没有人会这么做,然而这就是我们集体正在做的事情。
系统思考让我们去追问——在这些现象的表面之下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结构让我们个体即使不情愿、但大家一起做的时候导致了一些大家都不想看到的结果?如果大家去从这些角度思考的话,就会看到很多层面的问题,比如,有限的地球资源和爆炸性的增长之间的矛盾,亦或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幸福之间的脱轨。
如今,大部分的发达国家生产的东西越多,GDP越好,并不代表着我们就会更加幸福。我们生产的越多,我们消费的更多,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加幸福。因此,这些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过,真正的系统思考还要进一步来想——根源性的问题是什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根源性问题就产生于我们身边,产生于我们思想的质量,与我们对于经济方面的思考模式有关。它包括了关于过去的经济方面的思考模式被应用到今天和明天的经济现实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问题。
今天根本性的问题或者变革,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变革来应对这三大鸿沟。这需要我们不仅转变结构,同时也要转变我们的思考。
思考模式,从那种以前的自我的角色转变出来,到一个更加宏大的角度,也就是考虑到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这种结构。换一句话说,即是对于所有人的幸福都要思考,都要意识到。
因此,我认为,如今社会上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帮助领导者——所有系统中的领导者——召集所有相关的利益相关者,并且让他们从那种只关心自我的运作模式转变到新的运作模式。我们称之为生态系统思考模式。这种模式是专注于所有人的幸福,简而言之,一种系统的愿景和看法。
当然,在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做到呢?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实验的问题,也就是在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在实验的内容。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这种“从自我到生态”的模式转变,将之应用于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这将是一趟旅程。
于是,我们不仅需要产生新的想法,而且要进行真正的实验,这就是彼得和我带到中国的内容和实验,来看看这种模式是否在中国也会有帮助。
变革系统,归根结底就是变革不同的关系

彼得·圣吉博士 “学习型组织”之父
也许奥托·夏默尔刚刚说的大部分的事物大家都知道,三大鸿沟是一种很优雅的总结方式。我们知道生态方面遇到了问题,我们知道当地和全球都面临了许多的生态挑战。同时,我们也知道社会方面的鸿沟,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看到这些现象,大家不需要旅游到许多地方就能看到一部分人拥有着与其他人不同的机会。
大家应该知道乐施会,它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之一。乐施会所做的事情之一是跟踪这些社会上的鸿沟。如今,他们也跟踪了一些人,这些人拥有世界上一半的财富,最近他们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全球最富有的62人坐拥的资产,相当于占世界人口一半、约35亿最贫困人口的财富总额。这非常荒谬,不过,还有许多其他令人惊讶的数据提醒着我们——这是我们集体所创造的一种不平等现象。
与此同时,这种鸿沟也提醒着我们,我们或许已经知道、但可能平时没有注意到的一些现象,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抑郁、一些不幸福,在如今社会中很多人都有这些症状。然而,我们却并不拥有平和或是自知之明,也就是对于人生的清楚的认识。我们的教育系统其实就是这样的体现,因为它表现出来的就是学生间的激烈竞争,大家当然都很清楚这一点,因为来自中国,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会很有感触。但是,其实最后我们还是要共存、一起生活,不是吗?
因此,我想说的是,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只是我们所表现的方式比较清楚,也就是让平时可能注意不到的一些现象说得清楚一些。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能成为这种我称为“全球性的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因为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学习如何转变系统,也就是改变造成这种不好结果的系统。当然很显然,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并不能向大家证明什么。不过,这真的是一种非常清醒的意识,也就是思考“如何带来完全不同的一种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种学习的旅程。
在许多不同的场合,我看到了这种转变在发生。比如说在商业方面,在很大的困境下创造很好的结果。
其实,“合作”这个词以前我们听的并不是很多,而如今在不同的产业中,会谈到一些合作。在食品行业这种合作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食品行业的公司以及非政府组织在合作,他们将之叫做“竞争前合作”。如果你的所作所为将会破坏这个系统的完整性,但是你需要依赖这个系统,那么,不同公司之间的竞争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需要不同的公司共同合作,从而带来产业生态的改善,比如在食品安全、提升水资源管理等方面。这听上去有些疯狂,但是这确实是食品行业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在这段旅程中学到了什么呢?首先,系统变革并不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大家听到系统的时候会想到很大的事物,想到电脑系统。一个人可能会说——“我们要改变系统的话,那么只有我们的老板可以改变”。
改变其实是一种内在的行动,它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旅程。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着全球的系统,系统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和思维模式中,在我们不同的情绪和信念之中。所以这些系统不仅仅是存在于“外在的”,外在只是内在的一个映像。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深度的变革是和我们个人息息相关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宏大的课题。我们可以从食品行业所发生的动态中观察到人们的思维也出现了比较深刻的变化。我们现在的商业不仅是赚钱,我们希望打造一个健康的系统,以此为基础才可以赚钱。所以,这种思维是非常深刻的一种变革。
其次,把这些系统进行变革,最终归根结底就是把不同的关系进行变革。系统之所以可以发挥作用,那是因为可以有很好的新资源的交流和分享。当我们把关系进行变革的时候,需要一些流程帮助我们去做。
当然,目前交互的流程还是有一些混乱,这点我们并不吃惊。如果你让艺术家解释艺术的创造是如何进行的,而舞蹈家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方法和点子,各个专业人士都会有他们的特殊方法,但最终,工作方法并不是一个机械化的程式,我们会通过一些工具和指导性的想法进行指引,推进相互的交流合作。
我之前也讲到了学习,我们如何促成真正意义上的学习?
我们都是在婴儿的时候学习如何走路,以及长大一点学习如何骑自行车。我们无论写下来——我们如何学习走路的?第一步是什么?第二步是什么?如果有小孩去学骑自行车,你可以告诉他——你这个脚放在这,那个脚放在那,他就会骑了吗?其实学骑自行车就是要不断的摔倒,摔了之后他会就骑了。
可能六岁的小孩说:“我现在不想要摔跤,所以不想要去学自行车。”所以,你如果想去学,你就需要去摔倒,你需要毅力与决心,你需要有这个意念去接受犯错误。
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慢推进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受控的、机械化的过程,它有一些指导性的框架。最终,我们需要把关系进行变革,奥托博士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进行了一些方法论的描述。
其实,我想讲的“复兴”,最终就是如何去表达未来的希望。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确实是很有挑战的,普通的人可能都会对这些问题感到一丝沮丧和绝望,可能会觉得目前很多变革的尝试最终是无用的。然而,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深刻的变革,所以我们面临着紧迫的任务。
展望未来,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生活在其中的未来,将会取决于我们自己现在对于未来的信念。
Q&A
Q:面对很难逾越的鸿沟,我们到底应该是正视问题还是逃避问题?
奥托·夏默尔:面对很多挑战,我们会觉得无能为力,大家往往所做的第一选项是否认,第二选项是抑郁。大家会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些事,因为这些事是全球性的问题。
有些人会开始抱怨,会开始责怪其他人,愤怒,也是另外一种反应。只有经过了这些阶段之后,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就是有人会思考——好吧,我们对这些问题要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到底是正视问题还是逃避问题。这听上去很简单,但其实是一个很深邃的问题。
今年MIT的毕业演讲是演员马特·达蒙做的,我们都很喜欢那个演员。他在他的演讲中讲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些问题,然后他引用了克林顿总统的一句话。克林顿曾经接见马特.达蒙,并且给了他一句听上去很平凡的建议,虽然听上去很平凡,但是后来越想越觉得非常有深意,这也是马特.达蒙对MIT的毕业生所说的一句话——“转向你看到的那些问题,你必须要处理这些问题。”
转向你看到的问题——这就是让他感悟的一点,不要仅仅是否认问题、或是感到抑郁和愤怒,而是与现实相连,以更深的方式与现实相连接,并且面对问题。如果大家想想的话,这种思考的本质,其实也是给予我们一些有用的工具,从而真正的去面对现实。这种方式比所谓的否认、逃避或者愤怒更加有效。
我们对此也找到了一些条件,首先打开你的心灵,用一双非常新鲜的眼睛来看世界,然后,展开你的大脑。打开你的心灵,也就是用你的心所展现的那种智慧,并不是面对事情所呈现的“反应性的反应”,而是一种能够理解其他人想法的反应。另外,打开你的意愿,这意味着接纳和放手。
这些是内在的条件,它们将会带来变化,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当你转向那些你所看到的问题的时候,最后,你是会以感到抑郁和愤怒而结束,还是你会真正的去试图改变这些问题?
Q:你如何看待这三种鸿沟之间的关系?你如何看待用GDP这样主流的指标去衡量发展这个现象?
奥托·夏默尔:我们有GDP,这种是主流的指标。如果我们看看国际间的讨论的话,在过去四五年间,我们也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舆论在产生,也就是另外一种模式和指数。其中一个就是国民幸福指数。不丹在这方面得分非常高,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国家。很有趣的是,从不丹国王开始,他认为这种国民幸福指数比GDP更重要。
而另外一个我认为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它能够衡量所有的鸿沟。它是在你的国家,与你造成的生态足迹相比,你创造了多少幸福,也就是幸福除以生态足迹。
做的最好的国家就是哥斯达黎加,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过去140年来,他们对所有人提供免费教育。
第二,废除军队。勇于削减军费开支,因为军队并不会产生幸福感,把这些费用拿来投资于可以创造人民幸福的事物中去,好像我记得他们军队废除已经有四五十年了(1949年以来,哥斯达黎加宪法禁止设立常备军)。
第三,他们恢复了森林,以及有意识的将资源用于跨越生态鸿沟。于是,在过去二十到三十年间,他们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我对未来的期许,就是能把这两者连接起来,能够运用一些新的指标来跨越这些鸿沟。另外,能够通过一些工具来改变社会间的互动,然后推动创造性的结果,让人们把面临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
我认为还有一个阻碍我们应对问题的视点就是不现实的时间现实——人们认为政府可以马上解决问题,虽然世界上的很多政府想要解决问题,但他们却迫于应对选举这样的现状。
彼得·圣吉:我想在你的内容上再补充一些,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正在应对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人们有的时候期待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奇迹般的结果。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快速的实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在西方,我们慢慢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出现的这些问题,不大可能一夜之间就解决。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是谁?你很容易把这个手指指向政府说——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要去解决这些问题。
对于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是有责任,有所担当的,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解决,我们可以设定一些目标,在旅程的过程中不断的协同。我们认为可能需要花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才可以逆转气候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包括科学的角度。我们需要设定五年、十年之后希望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沿着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集体需要有共同的意愿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另外我也想强调一下,其实奥托所描述的三大鸿沟有一些微妙性。不能够单独去讲其中某一个鸿沟,我们只能同时去讲三个鸿沟。就好比这个冰山的模型,同一座冰山不能割裂开来讲。
因此,面对这个议题,我对中国有着未来的期许。中国确实也是面临着各种问题,中国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发展的态势很猛,不断跟上西方的步伐,不断地追赶西方,在很多层面,其实中国也是成功地追赶上了西方,尽管在其他的领域可能还没有追赶上。
我这次在中国的访问让我觉得中国可能有更高的信心水平。中国这边更有信心,这可能是不错的一个基础,来帮助中国应对独特的问题。中国同时有着全世界范围内非常独特的文化的资源库,包括对人类、艺术方面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包括如何把哲学应用到现实,中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成果。这些成果可能是最近的三百到四百年前实现的,所以是一些古老的成果。
“古老”这个词放到现代的语境下就是永恒的,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大部分的时间段,古老是一个褒义词。
对于这样一个古老的知识,它已经经历过时间的检验。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回到中国一千年或者两千年前的时光,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未来的的岁月里,我觉得基于“古老”的文化的进化可以发展中国的未来,我对于中国的期许就是中国在未来可以找到真正的自己。
Q: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忙碌,好像每天都在学习到很多新知识,然而,潜意识里会有一种不快乐,一种失去感。你们刚刚提到了自我与自我的脱节,你能更深入地阐述一下这一点吗?我们如何去消除这种不快乐感?
彼得·圣吉:首先,从技术上或细节上来看,可能与这个问题相关。我并不认为很多人每天吸收的是“知识”,大家获取的只是“信息”,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知识是能够做事的一种能力。可能你确实吸收到一些知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大量的信息与知识混淆。现在每个人都在吸收着很多的信息,但是这种信息有时候会让他们困惑,并不会让他们真正的理解事物。
对于自我与自我的脱节,可能很难给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会从一些角度去切入回答吧。二十世纪中期,有一位美国的哲学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在旧金山港当一名搬运工。他被认为是20世纪中期的非常重要的一名哲学家,他说过这么一句话,那就是“你无法通过消费过多的东西而获得快乐”。这句话可以来总结我们现在的消费文化。
如今的经济模式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它让人们一直处在不满足的状态,想要更多,永远有对物质的需求,但却无法获得幸福。我们应该让人们去关注那些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让他们变得幸福,发展出另外一种经济模式。
如果大家想想这种基于消费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其实就会发现一个很简单的真相——整个系统设计的目的就是让自我与自我之间断裂。也就是让消费者不要抱有怀疑的想法,不要真正的去反省他(她)到底需要的是什么。
在世界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中,当人们真正有机会去反省自己到底需要什么、他们最后需要什么的时候,其答案都是差不多的——他们的孩子、家人、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他们对人生的追求,他们的使命感,追求真正热爱的事物,以及对其他人有所贡献。这是我们在不同的地方反复看到的主题和内容。
如今,在一些国家开始有这样的反思消费主义与幸福的运动,从草根开始向上来建立一些幸福感。让许多社区以及整个地区的人思考“到底什么对我们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当然,物质方面的需求是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基础的需要,你没有基础的这种物质条件,这肯定是不行的,世界上还有许多人没有基础的物质,但是当我们至少有了物质基础之后,我们为什么还是想要更多东西呢?这就是为什么教育这么重要,但是很可惜,现代学校并不是为这样的思考而服务的。现代的学校是服务于那些目前现实的经济运作模式,为他们输送人才。
大家需要想一想——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我的一切潜力是什么?我想创造什么?我想要理解什么?我如何贡献、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这些是非常经典的一些问题,这些是真正的教育应该问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做出一些改变并不简单。
我认为困惑始于这样的发现,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复杂性与现实性。最初的切入点就是要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问问题。
Q:有时候会发现冰川底下其实很固化,很难向下走。我们如何消除这种僵化,延着U型一边下去呢?
奥托·夏默尔:我们还是要回到刚刚提到的那个问题——幸福的根源是什么?主要的根源,比如说包括我们与其他人的联系,我们与自然的联系,我们与自己真正的使命感之间的联系。而最后一方面是给予、付出,也就是说——对别人的付出,对给别人带来幸福感的付出,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好处。这其实挺让人惊讶的。
如果我们看看企业家精神,当你在采访、研究他们的故事的时候,几乎他们每个故事最开始产生这种火花、灵感的时候,几乎都是心与心产生相连的时候。这意味着这我们深层次的创造力与企业家精神是我们心灵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往往被大家忽略。
然而,这种同理心正在减少,不仅是在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美国的一个大学曾经做一个研究——通过几十年来测试人们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他们发现,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这个同理心的普遍水平在下降,这可能就是你所提到的“固化”这个现象。
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事情,我和一名学生交谈,他在名校受到教育,但在同理心方面,比如对一些难民的困境、或者对于那些比他不幸的人们所产生的共鸣,他完全是一片空白。
我认为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今的技术让我们能够下载更多的内容,我们困于一种泡沫之中。
而下一个十年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我们如何运用技术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现象,也就是利用技术让我们去接触到更深层次的情感,也就是与同理心、共鸣相关的东西,把你的心灵当作一种感情器,与其他人、自然产生共鸣,通过开放你的心灵,你才可能与其他事物产生共鸣。
我认为我们的教育系统只关注于教育我们的大脑,却在心灵方面完全空白,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